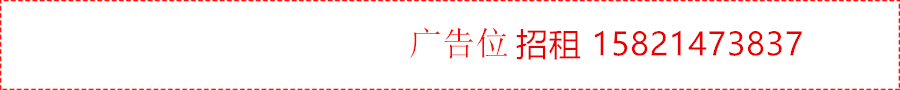兰亭集序/傅抱石画作
王羲之写此文时,已是51岁高龄,书风已达巅峰,是其书风成熟时期的代表作。
这一年是晋穆帝永和九年(公元353年),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,按古俗,人们要到水边祭祀,以祛除厄运,这就是本文所说的“休憩时”。
这天,天空晴朗,空气温柔。在山阴(今浙江绍兴)兰竹山下,举世闻名的“言辞落地,如金石之音”的“才子”谢安,哲学造诣深厚的名僧支敦,以及王羲之父子等四十一人齐聚兰亭,分坐溪水两岸。溪水蜿蜒曲折,盛满美酒的酒杯被这场雅会的“司仪”放在溪水之上,从上游飘洒而下。酒杯落在谁的前面,谁就要饮酒赋诗。参加这场雅会的名流们兴致勃勃,一共写了三十七首诗。三十七首诗结集成书,大家一致推举王羲之作序,从此便有了流传千古的《兰亭序》。 除了王羲之作序外,孙绰还写了《兰亭跋》,也记录了这次盛会,不过没有羲之的名气大。孙绰也是名字被载入中国古代散文史的人物。
我想,羲之当时是有些醉意的,他用蚕茧纸、鼠须笔写字,一气呵成,仿佛有神助一般。所以,《兰亭序》无论是文笔还是草书,都自然而随意。潘伯英先生说“醉时所作,最是天真无邪”。唐代何延之《兰亭笔记》记载,羲之醒来后,想再写,却得不到当时的神韵。或许,这也可以作为艺术上“酒神精神”的例证吧?
可惜的是,如此至高无上的书法巨作的真迹却随唐太宗李世民陪葬,并被带入其墓中,我们无缘见到真迹,所能见到的,也只是复制品而已。启功先生在《兰亭帖考》中,将现存的重要复制品归纳为两类:一类是宋代丁午出现的石刻本,一类是唐代的临摹本。启功先生整理了历代流传下来的《兰亭帖》的各种临摹本和各种古话,剔除了各种可疑的说法和明显附会、无关的东西,对今天我们看到的王羲之《兰亭帖》的临摹本,作了比较简明清晰的说明:《兰亭帖》在初唐时便入宫,许多书法家都临摹过,后来真迹随昭陵陪葬,世间流传的只有临摹本。 北宋时,在丁午曾发现石刻本,此本较当时所见本更为精练,为当时文人所珍视,唐代本亦与丁午石刻本并存。丁午本因反复捶拓,笔触已渐淡,字体较为僵重,而水墨本则笔触较丁午石刻更流畅,字体更为流畅。后人推测丁午石刻本为欧(杨勋)所摹本,其余为朱(遂良)所摹本。
但历来有人认为流传至今的《兰亭帖》并非王羲之手笔。清末顺德人李文天持此观点。李文天说,古时右军字有“龙跳天门、虎卧凤宫”之说,所以世上若无右军书法亦无妨。若有,“必与《爨宝子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相近,东晋以前之文字,与汉魏隶书相近,与时俱进,不能是梁、陈以后之体。”李文天所引八字,出自梁武帝《书评》。 同时代的黄永年先生也曾引用梁武帝《书评》中“王右军文笔,字迹遒劲”的句子,认为今天所见的《兰亭序》是梁、陈二人所作。这也是一种看法。但这些看法并不一定可靠。所以在书法史上一直没能占据主流。
我们再看王羲之的兰亭序,清雅、空灵、自然,28行324字,洒脱自如,就连重复20多次的“之”字,也是千姿百态,字相同,意义却不同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评价羲之的书法,“说者言其笔法如浮云,又如惊龙。”这的确是一句正确的评价。当代的沈尹默先生说羲之的书法“刚劲挺拔,行云流水,秀美静谧”,“美玉坚毅,宝光蕴于内”。这样的书法,即使不是羲之所作,又怎么会影响其艺术价值呢?但毕竟还是羲之的手笔。
王羲之是行书的创始人,《兰亭序》是王羲之书法风格成熟的代表作,这两句可以作为《兰亭序》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价值的主要体现。
故宫博物院藏《兰亭序》因上盖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,故被称为“神龙本”,相传为唐代冯承素所书的双钩勾填本,纸本。按照启功先生的分类,这应该算是流传下来的一种“唐本”。启功先生在诗中写道:“幸得唐本血脉存,白麻纸上神龙小印”。启功先生认为,此“神龙本”忠实地复制了原作墨色的深浅,“在现存的兰亭本中,当为最佳本”。至于是否为冯承素所抄,则无法证实。
南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“七十六志”篇中,有关于王羲之与《兰亭序》的记载:
当有人将他的《兰亭诗序》与《金谷诗序》相比较时,王右军很高兴,并认为他可以与石崇相提并论。
这段话的大意是,王羲之得知有人把《兰亭集序》比作《金谷诗序》,将自己与石崇相比,十分高兴。石崇的《金谷诗序》作于晋惠帝元康六年,即公元296年。石崇在河南金谷涧邀请三十人到自己的别墅里,为西征将军王旭送行,昼夜宴饮,饮酒赋诗,编成诗集,石崇便写了《金谷诗序》。石崇是渤海南皮人,聪明才智,征吴立功,封为安阳乡侯,能诗善文,这篇诗序名声大噪。所以王羲之“十分高兴”。
不过,当今文学史家对羲之《兰亭序》的推崇,远甚于石崇《金谷诗序》。《金谷诗序》自然是一篇佳文,也代表了“序”体裁的“新变”。但史学家认为,直到羲之《兰亭序》之后,序这一体裁才彻底从传统的集序、单篇序中独立出来,成为文人独有的诗文活动的“序”,并在南朝时期得到延续。此后,“赠序”等文章也沿着羲之文开辟的方向演化,达到了新的境界。见李山先生《中国散文通史魏晋南北朝卷》。 郭毓衡先生说,羲之序中描写山水,“天朗气爽,风轻柔”已是流传千古的名句,“散文自汉代始有描写山水之文,六朝亦可谓‘山川繁盛’之文,羲之文即为一例。”这也是从文学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待羲之的杰作。
既然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有如此高的文学史意义,那么鉴赏力极高、品味不凡的南梁昭明太子萧统,为何没有将此文收录进自己的《文选》呢?钱钟书先生在《管子编》中分析过这段文字,认为羲之的序“直抒悠然,不多思虑,短小精悍,言意重重”。只着眼于孤立的单篇文字,自然不能尽如人意。昭明太子不收录进《文选》,也无可厚非。钱钟书先生也推测:“难道羲之心思专在书法上,写文章原本是副业?”羲之本意是书法,写文章是书法之外的副业。这种推测也有道理。 当然,若从文学史的演变,或文学风格史的角度去看待,对羲之序的评价自然会有所不同。
南梁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》,在上引注后所作的注中,他又加了另一版《兰亭序》,名为《临河序》。除文字上有些不同外,结尾处多了几句:“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成功等二十六人作诗如下。前余姚令会稽谢生等十五人,不能作诗,各罚酒三斗。”文学史家推测,羲之作此序时,并没有收录这些句子。编纂成书时,才加上这些句子,“以合序意”。但若将这些句子加到羲之的书法作品中,“则觉有余”,这种解释合情合理,也合情合理。
奚之的《兰亭序》在书法史上和文学史上具有双重价值,尽管当时奚之只是把写作当成副业。
王羲之生于西晋泰安二年(303年),卒于东晋太元四年(379年),其琅琊王氏自北而南迁徙,历来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名门望族。
据潘光旦所言,中国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发生在南北朝时期,即“永嘉南迁”。其结果“最显著的就是长江下游人才文化的富集,而人才的富集显然是文化富集的一大原因”。山东琅琊王氏就是在这次东迁中南迁的。王羲之在东晋时任江州刺史、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,所以又称“王右军”。“永嘉东迁”,大家族南迁,北方发达的中原文化也随着南下的北方人定居南方。南北文化在这个时代进行了大融合,也引发了江南文化的蓬勃发展。 《兰亭序》也算得上是一个山东人迁徙江南,对江南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。东晋以后,江南文化在北方逐渐超过中原,唐宋元明清以来更是遥遥领先。近代,东方西化又一次引领潮流,吸收西方文化,另辟蹊径,不断创新。
七八年前我曾到临沂王氏故居游玩,近几年又到绍兴兰亭游玩数次,在先贤们留下足迹的地方,望着青山、想着流水,不禁感慨万千。
光明日报(2022年4月8日第16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