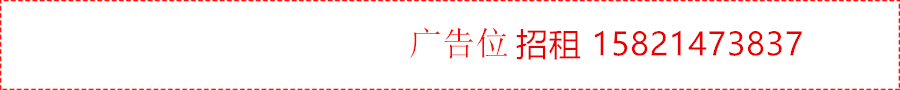01/
“残破的身体”的含义
关于“破体”的最早记载,可追溯到唐代徐浩的《书法论》:“周官有六书,教国学子。书法起源甚久,程邈改隶,邯郸传楷,作品简练简练,无功用。后仲善楷书,张芝善草书,右军善行书,孝陵为破体,皆妙于时。近世萧、雍、欧、禹皆传书风,朱、薛已衰,自蒯以来,无有批评。”
文中只陈述了钟、张、奚、冼四家所擅长的书体:钟繇楷书,张、奚、冼擅长的破体,但并未说明“破体”的含义。
什么叫“破体”?直到张怀瓘的《书礼》才有了更详细的论述:“子敬才华横溢,学识渊博,除行草外,另辟一派。行书非草非楷,离方脱圆,介乎季、孟之间。楷书谓之行书,草书谓之行草。子敬之法非草非行书,于草书流利,于行书开阔,于草书介于两者之间……在笔法中,为最雅的一种。”
王献之《嫁书》
正如张怀瓘所说,王献之在行草之外,又创造了一种新体,不是行草,不是楷书,而是楷、行、草三者相融的新体,即“破体”。“破”是打破,“体”是字体。“打破字体界限,综合各种优点,创造出一种新体,就叫破体”。
02/
颜真卿破体书法的由来
关于颜真卿的书法学习方法、书风的形成、书法品质与品格的探讨颇多,但对其标新立异书风成因的分析却不多见。笔者认为颜真卿标新立异书风的形成与以下几点有关:隋碑的影响、对张旭、王羲之书法的继承、对民间书法的吸收以及其自身政治生涯的坎坷。
王献之后,断体书法有所发展,但并未大放异彩,始于隋代,最具特色的《曹植庙碑》即是其中之一。《曹植庙碑》又称《曹子建碑》,始建于山东东阿,建于开皇十三年(593年)。此碑以楷书、篆书、隶书相结合,笔法丰富多样,有隋代“紧斜”和“宽横”两种体式,宽阔宽敞的形体和向外扩展的笔法显露无疑。从整体构图上看,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比较近,各字的组合也比较协调。无论是楷书、篆书,还是隶书,三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。
《曹植庙碑》局部
虽然史料中没有颜真卿师从此碑的详细记载,但二人构架宽广,风格相近,都是楷书篆隶兼用。作为唐代真正的创新书法家,他一定会关注这种特殊的书法风格,并受其影响。朱冠天先生在《中国书法史·隋唐卷》的论述中,就曾印证这一观点:“颜真卿《裴将军诗》楷书行草杂篆,乃隋遗风。”
颜真卿对张旭书法的学习,不仅包括他的笔法和书法哲学,还包括对王献之破体书法的接受。王献之破体书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《十二月帖》,该书融合了楷书、行书、草书,三种字体通过渐变,在构图上形成强烈的对比,整体看上去自然而又别具一格。
王献之《十二个月》
此幅作品首先以楷书“十二月”三字开头,通过字形的倾斜变化引入“截”字,继而一改以往的规矩,步入行草的韵律。作品中字的大小、疏密的对比以及大面积的留白呼应了整个构图,尤其是帖末的“庆军”四字,通过拉长字形以及“军”字的竖笔,展现了奔放的笔法,与开头的楷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。
于是,断体书法便应运而生,但后来的发展却并不是特别顺利,甚至很少有人关注,直到中晚唐颜真卿的出现,才得以重新崭露头角,这与王羲之在唐代的经历有关。
初唐时期,随着王羲之成为书法大家,王献之的地位一落千丈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,审美观念由清瘦苍劲向丰腴豪迈转变,王献之书法再度出现转机,其具有时代特征的“外延”笔法再度受到关注,重回“四圣”之位。
孙过庭《书法经》记载:“自古善书者,有汉魏钟、张,晋末二王也。”“幼时注意书法,品味钟、张之余气,习习、贤之先规。”李思箴《书法跋》:“子敬草书,风雅于其父。”“钟、张、习、贤,皆超然卓绝之作。”
从当时著名书法理论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,王献之在中唐的书法地位,是王氏和王献之都十分推崇的。随着王献之地位的逐渐提高,向他学习的人也不乏其人。这时,张旭崭露头角,“有人以为张公是小王转世。”张旭不仅继承了王献之的连笔草书,还对其新风颇为重视。
张旭《胃痛帖》
以《胃痛信》为例,可见他的书法在王羲之的基础上更加奔放、自由,动静对比更加明显,连笔、个人情绪的表达都比以前好。同时也为向浪漫主义书风的转变打开了契机。颜真卿学张旭笔法,继承王羲之,深受二人的影响。
《祭侄文》的影响,从最后部分的草书可以看出来,也显示出“草圣”对其的影响,也显示出颜真卿在草书方面的成就。他的草书推动了楷书的流畅。此稿是行书与草书结合的天衣无缝;《争座图》兼具行书与楷书的兼容性。颜真卿成为又一位破体书法的践行者。
颜真卿在断体书法上的创新,也源于他对民间书风的接受。民间书风对颜真卿书法的影响,已有许多文章探讨。我在此不作详述,只陈述我的观点,“颜真卿对唐代民间行书的整理和改良——民间行书的提炼。这些因素(师王制、家传)的综合作用,造就了颜氏行书的特色——篆隶之味。”将篆隶的笔法融入草书、楷书作品之中,是颜氏断体书法的一大创新。
颜真卿《裴将军诗》
此外,颜真卿自身在仕途中的不幸经历也影响了他心态的变化。在与几位宰相的矛盾和多次被流放的经历之后,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自从颜真卿突然被流放之后,他一改官场闲暇时的惯常行为,开始寄情山水,沉溺于诗文,依靠佛教寻求解脱。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不能完全用正统的儒家思想来概括,一种崇佛的心态油然而生。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颜真卿的人生态度,也影响了他的艺术境界。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,我们不难想到他创作了《裴将军诗》。这样的“破体”书法是有道理的,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楷书作品被彻底打破了。
以上种种原因促使了颜真卿试图突破传统风格,加之颜真卿在楷书、行书、草书方面的成就,又为他创造出突破传统风格的楷书、行书和草书提供了条件。
03/
颜真卿破体书法的具体表现
颜真卿对断体书法的接受,早在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就已显露无疑,而且他一生都在使用断体书法。从他四十八岁时所写的《修书帖》和五十一岁时所写的《杂凤辞帖》可以看出,他早期的断体书法,无论是形式上,还是整体的气氛上,都与王献之的《十二月帖》比较接近。直到建中四年,也就是颜真卿去世的两年前,他七十五岁时所写的《凤鸣帖》,仍然在写断体书法,但这些书体断体书法与《裴将军诗》相比,显得有些苍白无力,很容易被忽视。
《裴将军诗》又称《送裴将军北伐诗》,现见宋忠义堂刻本,现藏浙江省博物馆。全文记述了唐文宗时镇守北方的将领裴敏的功绩,突出了将领作战杀敌的勇敢果敢。此作形式感强,字体以楷书、草书为主,大小、长短、粗细、粗细变化强烈。
此书行草取自楷书笔法、结构,兼有篆、甲骨文沉稳、厚重之风,同时吸收其老师张旭草书的奔放之风,富有创新性和丰富性。
分析《裴将军诗》的用笔,可以发现:草书兼有篆隶之笔法,转笔、圆笔并用。用笔多以笔心写,笔尖隐去,头尾隐去,笔画反平,在转折处、收笔处多用扭尖,以显圆润。如第三行的“将”字、第四行的“清”字、第七行的“何”字,收笔、连笔都到位到位,很少出现弱笔、落笔,充分体现了他从“印墨、锥汲沙、漏屋留痕”中学习的笔法。方圆笔画的运用十分巧妙。
在结构上,也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向外扩展特征。颜真卿的草书改变了王羲之的内敛笔法,同时吸收了篆、隶书圆润庄重的结构特点。如“制”字的竖勾竖笔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向外扩展的感觉。楷书的大多数字,重心都在字的下方,表现出一种稚拙的感觉,如第四行的“垓”字、第二十二行的“雄”字。
整篇作品巧妙地运用连体,将楷书与行书连为一体,既统一又富有韵律感。行书结构中明显可见张旭《古诗四首》的影子。如“将军”、“舞剑”、“归家”等字,展现出行书的清新之风,仿佛亲眼看到裴将军临阵杀敌的激动人心的场面。
张旭《古诗四首》部分
从整体构图上看,风格杂糅的作品,很难安排得井井有条,但颜真卿却把这种气韵安排得流畅自然,没有任何生疏或做作。整幅作品的行距大于字距,字的大小变化自然。同时,还有几处长笔,如第八行的“将军”,第十一行的“剑舞”,第十八行的“声响”,最后一行的“麒麟”等。整体构图规划合理,还留有大面积的留白。长笔周围的笔画较粗较重,与大面积的留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
每行末字与下行首字同体,整个构图自然而不突兀。清人王澍在《徐州铭》中说:“此书法兼有楷书、行书、草书之气;如篆隶之气,天下无双。吾谓之鲁公第一奇观,实不虚也。”
全篇通过粘连、衔接、交织、组合等手法一气呵成,平凡中蕴含非凡,险峻中蕴含正气,和谐中蕴含险峻。《裴将军诗》将楷书、草书两种静动风格完美结合,颜真卿的探索将断体书法推向了另一个高度——楷书、草书断体。在王羲之的基础上,夸大了书体之间的对比,也加入了不同书体的融合,是“古法新意”的新创。
04/